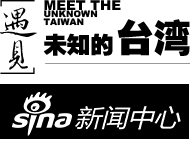遇见未知的台湾
两岸有多远?远到即使只是一回头,便可能如大洋之遥,万里相隔;两岸有多近?近到只需一声轻轻呼唤,便能有心心相念,手足离愁。
习先生说,两岸是兄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马先生说,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余光中说,两岸之间,其实只隔了一湾浅浅乡愁。
上个月,新浪新闻跨过海峡,努力用最多元的视角,用文字、影像、无人机及360度视频,在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忠孝东路、圆山饭店、阳明山、渔人码头以及眷村,近距离观察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台湾。
有人说,三代人的时间足以融入一方水土。
张绍琰是典型的眷村三代,出生于1991年,爷爷张达五随国民党到台湾的第43年。
他讲一口带有台湾腔调的普通话,说自己是“都市人”而非“当地人”,因为不会讲闽南话。他把眷村当做自己的故乡,坦言“对爷爷的老家没有情感。”
从记事起,眷村就没了竹篱笆,山东馒头、牛肉面也在台湾街头随处可见,不再是眷村“特产”。
他上私立学校,班级不再以你是“工人的儿子”还是“军官的儿子”来划分。张绍琰说,他们这一代人眼中不再有眷村内外,只有城乡差距。
张绍琰所在的北投中心新村,是全台湾886个眷村中唯一一座至今仍有人居住的村落。但2016年6月,这最后一处装满故事的的村落也要被“改建”,淹没在高低林立的楼宇中。
自此,作为一段特殊历史产物及文化象征的“宝岛一村”,将随着老兵的离世与城市发展的进程变为另一段历史。
这让90岁抗战老兵顾黄生面临第二次“迁徙”,老人低头抚摸着手心里的青天白日勋章嘟囔着“不想走也不行,以后不能回来了。”就像第一次从江苏老家随国民党到台湾一样。

眷村的夜晚
百万国军落脚台湾 诞生近千眷村
“听说那个地方没有冬天,说的是闽南话,沟通困难。我真无法想象未来的日子。”电影《风中家族》里,国民党军人盛鹏在搭上开往台湾的轮船前,有这样一段独白,是他写给家中待产妻子的信。
1948年2月,22岁的顾黄生是陆军也像剧中的盛鹏一样,随国民党来到台湾。后来他知道,那些年陆续涌进台湾的“盛鹏们”及家属有一百多万。
这些人被安置在部队周边,“军人统统住在这里,部队叫你就随时回来。”北投眷村的里长张聿文将其称之为台湾近代史最大移民潮的聚落,“眷村没有血缘关系,承载着中国庶民生活文化,小老百姓在台湾生根发芽。”
据台湾“国防部”出版的“国军眷村发展史”记载,全台湾有886个眷村。
每一个眷村都是围绕所属军单位而存在的。就像四四南眷村生活的军民都服务于四四兵工厂,北投眷村的单位就是一墙之隔的军医院。

在眷村生活的老人
曾有一次机会,顾黄生可以跟部队再回到大陆,最终却因生病错过了那唯一一次跨过海峡的机会。
“民国38年(公元1949年),我们部队要走了,医院里的人说我的病没有好不可以回去。他们说你住在这里,等你病好了我们将来送到你大陆去。”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小半年,而在台北却逗留了近70年。
张聿文说,顾黄生的病是因为水土不服。这一年,张聿文的父亲张达五也到了台湾,在北投的军医院做政治工作。
病好后的顾黄生留在这所军医院中开车,每三天到蒋经国的府邸取其假牙,再送到医院进行清洗和修补。
刚到眷村时,晚上一两个人不能到太远地方去,“容易被外面人砍掉。”顾黄生说,“他们(当地人)把我们称为‘外国人’,说我们是流氓政府。”到1949年下半年,“他们说你们也不要杀我们,我们也不打你们。后来东南西北都可以去。”
-

眷村的夜晚。摄影/邹璧宇
-

眷村的夜晚。摄影/邹璧宇
-

眷村的夜晚。摄影/邹璧宇
-

眷村老旧的房屋。摄影/邹璧宇
-

眷村老旧的房屋。摄影/邹璧宇
乡愁难解 听寻人广播哭着无法入眠
“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这是当时国民党军人心中的一个时间表。
他们被要求不准结婚、不准退伍。“老子手上有枪,不准结婚就拿枪开你,要不然就打自己。”张聿文说,当时有很多这样的事发生。1952年,北投的军医院成立了精神科。
“大概民国49年(1960年)左右,上面开放了说可以结婚。”从那时起,顾黄生就知道,“打不回去了。”
1962年,顾黄生娶了个台北市区的太太,“普通话讲得好。”此后,顾黄生分到了北投眷村把口的房子,是宋美龄妇联会盖起的七栋房子之一。
1976年,顾黄生从部队退役,在家里开起了杂货铺。“这个老家没法想了,咋想都没有用。”

在眷村生活的老人
两岸开放前期,台湾能跟大陆联系上了,张聿文发现往日威严的父亲“变成了一个无助的老人”。
“我爸听朋友说有大陆的亲人通过广播找儿子,他就开始听,晚上常常睡不着,哭。”张聿文把两手放在耳边,做出捧收音机的样子,歪着头咧着嘴。
1987年12月起,台湾允许民众到大陆探亲。第二年,顾黄生回了一趟常熟老家。他发现当初村里一起出去当兵的8个人,最后就只剩下他一个。
“回去就两个礼拜就回来了,生活、天气不习惯。”在姐姐和弟弟离世后,顾黄生就不再回大陆。“这里不冷,那边冷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似乎留住他的始终都是气候。
张达五却不敢回去,“只能到香港去打一个电话,跟大陆的姑妈通上话。”张聿文说,因为打仗的阴影还在父亲心里,以为又要回到战场上去了。“但他回去以后,哭哇。见不到父母,他又是独子,没有尽到孝道,无奈啊。”
张达五过世前,半年住台湾,半年住湖北。“因为大陆太冷,他受不了。”去世后,张达五被安葬在台湾。
“台湾的军人公墓,一个高尔夫球场,18区全部是墓园也不够,摆了多少军人在里面?”张聿文坐在石阶上,拍了拍膝盖。

屋里的陈设
“竹篱笆里的春天” 与大陆一样的生活
张天智将眷村的意义与万里长城划等号,“都是战争的产物。”
1949年,父亲带着不到三岁的张天智及妻女来到台湾,落脚四四南村。所以张天智算个“非典型”眷村二代。
作为当时全台第一座眷村,四四南村有指挥所、碉堡、防空洞、防空壕,“战争上要有的这儿都有。”在张天智的记忆中,小时候的眷村全民皆兵,制造武器,准备反攻大陆。
四四南村中居民80%以上都是山东、河南人。虽然自己的父亲是湖北人,但不论是山东、河南话,张天智随口就来。
最初眷村的房子以竹子、篱笆和稻草改建,台风多雨大,篱笆被水泡塌陷后军方又改用甘蔗板。“当兵从部队回来后,在家睡觉,隔壁有一对夫妻打架,我睡着睡着,一个拳头就过来了,我一辈子忘不了。”后来竹篱笆成了眷村的标志,张天智把眷村里的生活称为“竹篱笆里的春天”。
这里有山东馒头、茶叶蛋、炒花生,“小孩越生越多,为了生存把大陆的手艺带过来了,推着霸王车卖包子馒头当副业。”
张天智说,最初的眷村生活和大陆一样,吃饭也要靠粮票,“没有粮票领不到米。”就连小孩子玩儿的游戏都一样“滚铁环、弹珠、跳橡皮筋‘满地开花21’。”
三四年前,大陆来的小学生穿着制服到台湾,张天智看到吓了一跳“这不是跟我小时候穿得一样么?领巾是红色的,我们是蓝白红。”

在眷村生活的老人
眷村第二代:总想着“打回大陆去”
张天智4岁就读书,后来班上还有8、9岁孩子在读一年级。“那个时候阶级观念很重,甲班可能是住在外面的本省人,乙班是军官的儿子,丙班是工人的儿子,分得非常清楚。”张天智是工人的儿子。
眷村子弟生来背负着“反攻大陆”的责任。后来张天智去当兵,成为少校,“我就是要打回去的那一批人。”他们小时候教育目标就是打第一仗、立第一功。“‘今年我们在这里喝酒过春节,希望明年我们就在北京,喝上‘凯旋’的酒。’小时候的功课就这样,写文章。”
张天智说,他们眷村的二代参军比例在80%以上,“小时候一说没有饭吃,就‘当兵去’,就这样。”
1988年,四四南村开始改建,1999年,居民陆续住进对面的高层大楼。只剩下4栋房屋留存为遗迹。如今,穿梭在这4栋低矮房屋间的窄小巷道时,总能遇到几位带着外乡口音的老人,他们是曾经的眷村居民。
张聿文说,眷村是一个家的概念,安定下来就不想动了。
北投眷村在1979年时说要改建,“早期要所有眷户100%同意,当时有一两户不愿意,所以一直到现在。”张聿文现在觉得是对的。
马上腊月了,张聿文搓一搓手,“在以前,眷村每家要开始做香肠腊肉了。所有小孩做美食评鉴,偷吃啊,木柴捡一捡就烤,今天吃谁家的,明天吃谁家的。”这样的生活早已一去不复返。
一天下午,张天智喝了很多酒,坐在小板凳上张嘴吞下几颗红红绿绿的药片,说想一直停留在小时候的眷村生活中。“我在外面打架,衣服破了,我妈一定骂我,回来之后邻居的妈妈看见了,给我把衣服缝好,我穿回家。”

张聿文说,眷村承载着中国庶民生活文化
眷村第三代: 希望眷村可以重生
为了迎接张绍琰的出生,张聿文在家里多接出了一间铁皮屋。
随人口增多,眷村的房子也不断向外膨胀,使街道变得越来越窄。张绍琰说,小时候和邻居一起只能在村口的那条路上玩。“羽毛球一打就打到隔壁家去,隔壁没人住,球就找不到,羽毛球打没多久就吹了。路是斜的,一没接到,球就滚到马路上去,光捡球就检饱了。”
张绍琰没有经历过外乡人与当地人生活磨合的过程,“那应该是在第一、二代年轻的时候。” 比如村子里有很多奶奶是闽南人,但却不讲闽南话,“会被爷爷骂,因为爷爷听不懂。他们年轻时要磨合很久。”
他也没有像父辈们被当地人称为“老芋仔”(二次大战结束以后迁居来台的外省人)。他作为一个“都市人”在台湾长大,读私立学校,说当地口音的普通话。
他把眷村当做自己的故乡,“台湾省台北市北投中心新村”这个地址从小写到大,不会像自己的父辈们一定要把“籍贯”那栏写下大陆的省市。“对爷爷的故乡没有情感,就像一个人搬很多次家。那是他从前住过,我去过就等于游玩。”张绍琰说,现在跟那边的亲戚只是“偶尔微信联系”。
“现在没有眷村里外,只有城乡差距。”张绍琰说,没有同学知道他住在眷村,“就算我去提,他们也不会有任何感觉,很多以前住眷村的人早已搬进大楼,只是我们村比较特殊。”
6月份,张绍琰也要像那些早已住进大楼的人一样搬出眷村,这对于“90后”的张绍琰而言并不遗憾。“没有什么留恋的,我比较冷酷。我不会哭、伤心。”但他又说“遗憾的会是,我搬走之后它被拆掉,我希望它可以重生。”
现在,张绍琰正同父亲张聿文一起,竭力将北投眷村保存下来。“我不希望它商业化,变成一个失去温度的地方。”张绍琰希望晚上可以有人住在这里。“如果这里没人住,那一百年后,眷村的文化就死了。”
他说眷村的文化是既定存在的东西,你只要住进来这里,就会表现出它的文化。“挨家挨户,做什么别人都听得到,所以要保持良好的关系。我必须要叫得出整个村的名字,我认得他,他也认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