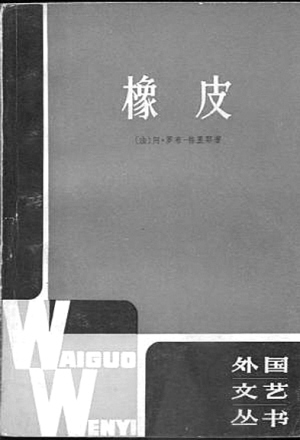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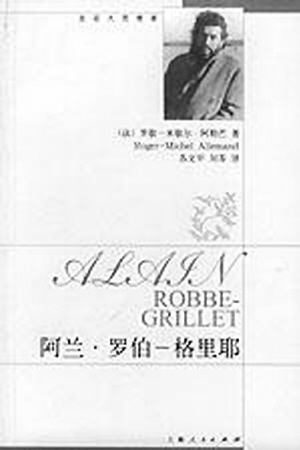 |
 |
2005年秋,阿兰·罗伯-格里耶来京期间,与本报记者有过一段短暂对话。当时他称,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有人“读懂”自己的书,他视之为“一种胜利”。他告诉笔者,因为不理解这个世界,所以动笔写下来。然而写作不断,他对世界却“越来越不理解”。
世界也不大了解他。两年多之后,罗伯-格里耶告别了人世,留下的最近一本出版物:《感伤小说》,因题材、写法出位而得恶评如潮。对于这位以推广法国“新小说”运动著称的先锋作家,网上铺天盖地的媒体悼文———当中包括了法国、英国、德国与美国主流媒体,在肯定了这位法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之余,同时也表达了对格里耶为人、从文的不理解。在一个似是适合盖棺论定的时刻,赞美之词在格里耶身上并不过剩,争议的声浪反倒比作家生前更无忌讳。
迄今读到最严肃、来自“权威”的悼词,仅有法国总统萨科齐一家。萨科齐办公室形容罗伯-格里耶:“无论是对亲密幻想的表达,还是对概念清醒冷静的分析,都一样自然自在。”并称“法兰西学院失去了一位最杰出、且无疑是最叛逆的成员。……法国知识分子界与文学界从此失去了整整一代。”
若要提到法兰西学院,法、英、美各大媒体对总统先生的这番溢美可不完全赞同。媒体们都不约而同提到显示格里耶自负个性的典型例子:2004年,格里耶被以守护“美丽的法语”为己任的法兰西学院推举为院士。在被推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后,他指出因为自己是“新小说之父”,而不需要遵循学院传统去套上绿制服、戴鸡冠帽、佩剑;作家对此的“解释”是:“他们应该知道,荣幸的是他们,而并非反过来。”罗伯-格里耶从未列席过法兰西学院的任何一次会议,因此学院最终并未公认他为正式的成员。
“新小说之父”罗伯-格里耶去世前的“绝笔”,似乎成了败笔。法国的《时报》称,罗伯-格里耶于2007年出版的《伤感小说》,虽被作家自称为“成人童话”,并算不上是他的一部“作品”;然而由于书中内容大写虐恋,终究是捅下了不大不小的马蜂窝,令法国文坛、传媒与批评界侧目:怎能如此为老不尊!
事实上,已有众多批评家指出,罗伯-格里耶在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作品,大多与“叙事复杂的色情小说”无异。而出版于1977年的《有镜子的寺庙》,就因为包含有年轻女子的艳照而在法国被禁。而2004年,罗伯-格里耶之妻出版了描述两人初婚生活的回忆录,当中披露了作家常将“萨德”(虐待狂)幻想付诸现实,引来公众议论纷纷。
《纽约观察家》、“路透社”认为,罗伯-格里耶这个“口无遮拦的孩子”,是“二战后法国一代知识分子的CULT偶像”,他的“注册商标”是一种摒除情节、角色塑造与情感的小说。结果是引出了一种半哲学式的小说创作手法———没什么实质事情发生,但包罗了庞大的思虑与想像。
但正是这样的手法,从《橡皮》到《嫉妒》,令罗伯-格里耶常被评论界诟病为“形式大于内容”、“言之无物”。英国《独立报》提及,法国思想大师罗兰·巴特也算是把罗伯-格里耶带上路的伯乐了。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提及晚辈的创意,但也不否认罗伯-格里耶作品形式大于内容的特质:“罗伯-格里耶是个视觉小说家,他的洞察力精彩绝伦,但却充满了不确定。”也因为这一点,令“作家罗伯-格里耶”毕生平行地与“电影人罗伯-格里耶”为伴。
在英美、尤其是美国的媒体眼中,罗伯-格里耶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电影人。“路透社”认为,罗伯-格里耶甚至并不广泛为法国之外的欧洲人熟悉。这是因为,如英国《时报》所写:作家的小说虽然多有英译版,但他推广的“冷感”小说,通常缺乏叙述的焦点,而总是围绕静物喃喃自语,因而从来不曾做到受众广泛。罗伯-格里耶为法国“新浪潮”导演阿兰·雷乃写下脚本的《去年在马里安巴德》(Last Year in Marienbed),于1962年率先在美国上演,因而被美国媒体视为阿兰·罗伯-格里耶最为人熟知的作品———还获得了一项“奥斯卡”提名。《时报》认为,罗伯-格里耶在理论概念上所得的荣誉,令他极适合于在对应媒体时自圆其说,并在学术研讨会上侃侃而谈,但就是离大众远了点。“倒是他在诺曼底的家所种的各类仙人掌更引人关注”。但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则认为,罗伯-格里耶这名字的低调,正是“现代主义的极致体现”。
英国《独立报》写道,罗伯-格里耶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成为“新小说”阵营中最激进且最“商业化”的一位。报道称,罗伯-格里耶的写作生涯建立在一种狡黠且可笑的悖论之上: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小说去解除小说的传统性质,但“他实践得如此聪明而投入!”
不过在1984年至1994年之间,罗伯-格里耶陆续出版了自传式小说三部曲,在书里温和地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对小说与电影中的现实主义的摒弃。但他却承认想像力的优点,并不会因为科学观的介入而萎缩。作家还宣称,如果能够防止我们将幻想付诸行动,那么通过小说或电影去幻想便是件好事。晚年的罗伯-格里耶已是公开站在“文学”的一边,甚至千里迢迢到美国的各大高校去任教。
相对于别国的“无情中立”,法国本土的媒体向文坛老将表达了敬意:《世界报》博客专栏作家、记者皮埃尔·阿苏莱(Pierre Assouline)写道:“怀念格里耶的自由,他的幽默,他的智慧,他的渊博与他的独立精神。” 《费加罗报》认为,罗伯-格里耶不仅是位作家,也是位文学理论家。他不仅刷新了小说的写法,也刷新了人们写作与阅读的经验。罗伯-格里耶是终身的“学院派挑衅者”,他给文学历史留下了“一种有特色的写作理论概念”。
还有一种说法也颇有代表性:文学评论家约翰·弗莱切(John Fletcher)称罗伯-格里耶为“法国最重要———却未必是最伟大———的作家,他毕竟改变了世界文学的面貌”。
编译/本报记者 张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