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派克
[环球时报记者 夏温新]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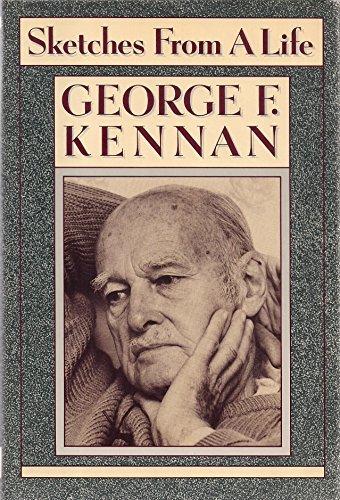
詹姆斯·派克编辑的最后一本乔治·凯南的书——《生活速写》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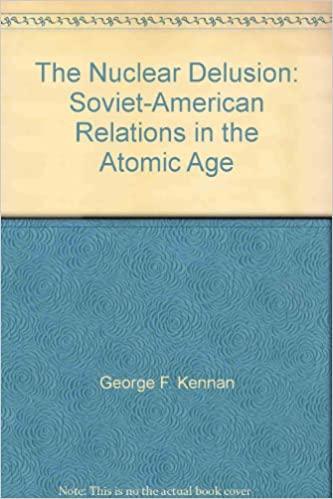
《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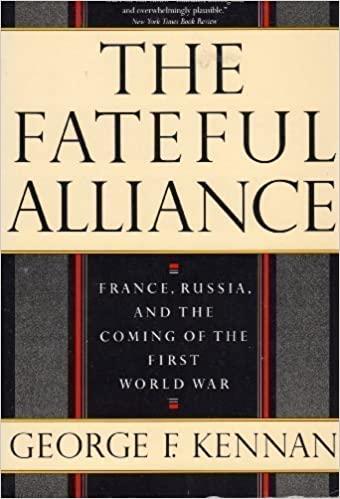
《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