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远视与短视
学院派“远视眼”患者们早已孕育出了一种特有的理想主义——如果我们放眼未来,关心未来,那么未来一定会更好。

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有份看起来非常完美的简历。
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还曾是克林顿政府的经济学幕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一位政治与经济经验都如此丰富的学者,似乎理应对市场和资本主义有全局式、跨视角、超越意识形态的看法,而斯蒂格利茨学术生涯的很大一部分,研究的也正是资本市场的非理性、不完美与信息不对称等。
悖论就在这里出现了。年已76岁的斯蒂格利茨,今年出版的新书《人民、权力与利益:愤怨时代的进步主义经济学》(People, Power and Profits:Progressive Economics for the Age of Discontent),读起来好像某种只能在全员经济学家的乌托邦社会里成立的教义。哪怕这位大学者在自己的研究当中可以充分意识到,人类无论从事经济还是政治活动都充满非理智的行为,他还是不能打心底里接受人类本来就错误百出这一事实。
斯蒂格利茨像后特朗普时代的很多民主党“精英分子”一样,陷入了认识论地基被连根拔起的愤怨当中,全然不明白在他批判资本市场上百分之一的人口掌握百分之九十九的资本的同时,知识市场(姑且叫做市场)上百分之一的人口也同样掌握着百分之九十九的话语权——他本人就是其中一分子。在他呼吁绿色经济、根据种族改变经济结构、复兴对真理的追求、创造更为包容的人才市场等的时候,默认这些是“普世价值”,是“人类常识”,甚至是经济增长与生产力的主要源泉。
然而,资本主义——一种目前看来适存能力极强、受众群体极其庞大、当然也非常不高尚的制度,并不多么认可这些价值观念。而斯蒂格利茨笔下的大多数并没有接受过精英教育的“人民”,是真的被代表,还是“被代表”?他们是否真有跟着斯蒂格利茨“进步”的意愿?
更奇怪的是,斯蒂格利茨这样的新凯恩斯派经济学家,总喜欢批判市场或者政府的“短视行为”,我把这叫做一种幕僚型知识分子当中很常见的“远视眼”。
在“远视眼”的瞳孔当中,未来总比当下重要,而三五十年后的未来又比三五年后的未来重要。他们很愿意为结果不可预知的所谓“可持续发展”而牺牲肉眼可见的眼前利益,在勾画经济结构的时候,喜欢把“我们的后代”或者“地球的未来”挂在嘴边。有且只有在往远处看的时候,他们火眼金睛,而面对当下的时候,他们眼前一片模糊。
举个例子,斯蒂格利茨认为让更多的女性参加工作,“从长远来看”会提高社会生产力,并达到更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没有提出任何政治上或者经济上可行的方法,能解决当下育儿成本过高的问题。
这当然不是说《人民、权力与利益》一书中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根据。
斯蒂格利茨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老工业城市盖瑞(Gary),亲眼目睹了外包导致的美国工业衰退,使得像盖瑞这样的城市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一蹶不振。出门到东部上大学的斯蒂格利茨,与没出门准备到本地工厂当工人(当年在美国当工人是正常的中产阶级工作,工资可能比大学教授还略高一些)的同学相比,命运因此也就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发生的故事,它不公平、不平等,甚至非人性。
斯蒂格利茨像大部分凯恩斯派一样,认为资本贪婪的本性在过去30年随着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政策而被彻底释放,大部分人的利益不再是政府的执政目标,反过来政府为大资本、大银行、大私募当着卑微的门童,运用里根发明的“涓滴效应”之类“巫毒经济学”劫贫济富。过去40年,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国人收入并未增加,医疗成本翻了三番,生活质量下降,更不用说斯蒂格利茨在盖瑞的老乡,他们面对的是大面积的失业与提前退休,且工业复兴的前景十分黯淡。
是否认同这些观点,是复杂的意识形态博弈。比如,最近几任美国总统当中,唯一对复兴美国工业有期望且不惜实施贸易保护来实现这点的,是特朗普而不是奥巴马或者克林顿——在凯恩斯派“远视眼”眼里,产业转型永远不可避免,全球化则更是人类的未来。斯蒂格利茨认为特朗普只是在利用老工业城市人民的焦虑,拿完了选票便不管不顾——这纵然是事实,但恐怕一个下岗工人显然更愿意听到的词是“复兴”而不是“同情”——靠研究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斯蒂格利茨,不该理解不了这点。
更进一步,斯蒂格利茨喜欢谈“绿色经济”,而绿色经济与盖瑞市的煤矿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认为老工业能通过研发,通过改革,甚至纯粹通过信仰,找到“绿色”的道路,实在是过分理想主义的思维。斯蒂格利茨也喜欢谈科技进步,他很明白科技进步(尤其是“长远”的进步)也意味着大量失业不可逆转,然而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书当中我看不出他支持传统工会的斗争模式。相反,斯蒂格利茨相信“宏观调控”——让大政府,或者说大政府里的大经济学家来负责调整产业结构。比如他认为,政府可以把因为IT、AI等高科技的发展而下岗的人们,调配到需要工人的养老行业、教育行业。如何让一个高中文凭的流水线钳工,当上需要硕士文凭的小学语文老师?
斯蒂格利茨虚晃一枪,因为像大部分没有底层生活经验的人一样,他并不明白这不是说说就能做到的。至于近年来在这方面很流行的“全民基本收入”概念,斯蒂格利茨完全没有谈到——对把就业率当作万丈光芒的指标的凯恩斯主义者来说,这种调控方式显然完全无法接受。
无论用民主党喜欢的种族、性别来衡量,还是用马克思主义者注重的阶级论来看问题,我们都能看到社会上确实存在大量经济上的不平等与资源分配的不公,然而新凯恩斯主义者比起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悲观情绪与激进态度要少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早已孕育出了一种“远视眼”特有的理想主义——如果我们放眼未来,关心未来,那么未来一定会更好——这是句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着实荒谬的话。不幸的是,学院派“远视眼”患者,如今恰恰是各国政府智囊团里的主流。这也是为什么更关心当下的大部分普通人宁可受垄断市场的那百分之一大资本的罪,也不愿意受垄断价值观(尤其是垄断未来价值观)的那百分之一大调控家的罪。
斯蒂格利茨书名里的“进步”是未来时态,但愤怨却是现在时态的。很可能这种状态将持续很长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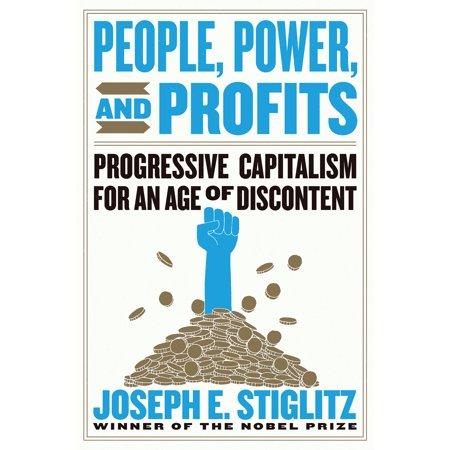
《人民、权力与利益:愤怨时代的进步主义经济学》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