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王林亚︱解放动物何以可能?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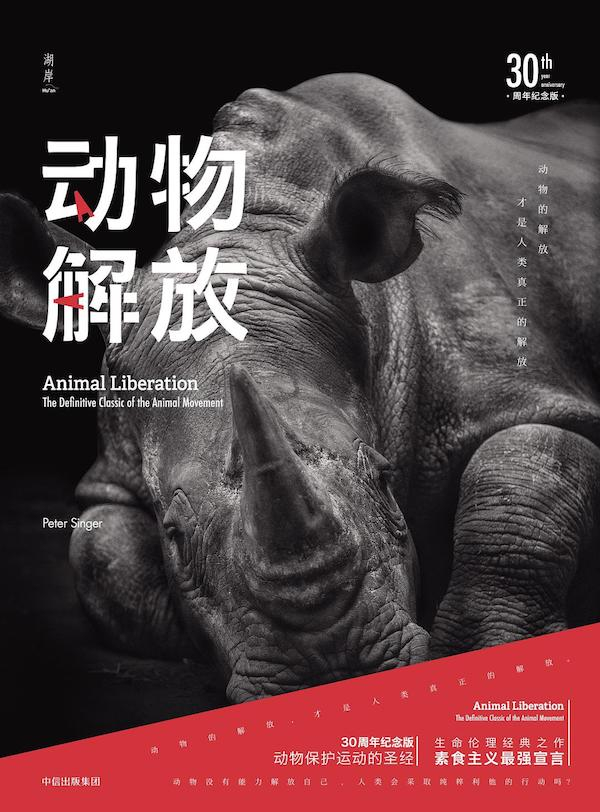
几千年以来,人类中心论价值观一直主导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毋庸置疑,这种价值观在改变人与自然的原始关系、提升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上曾起过决定性作用。但之后这种价值观逐渐变得极端化,充斥着人类利益居于绝对首要地位的论调。甚而,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认为,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界的动植物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任何谈及人与自然界之间伦理关系的论断都毫无任何意义。
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征服和开发自然环境一度成为掌权者的主流话语,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如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美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西部开发等。此外,这种价值观还给动物带来深重的灾难。历史上各类动物制品极大地满足着人类的物质需要,如北美早期发展史上著名的毛皮贸易,极大地满足了欧洲贵族上层社会追逐时尚的需求,但却是以北美大陆的海狸、野牛等毛皮动物的灭绝为代价的。
其实,“动物为人类食用”由来已久,确切地说,人类天然地将动物置于从属于人类的地位,这种态度根深蒂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主要根源于犹太教和古希腊文化两个传统。《圣经·创世纪》宣称,在上帝创造的所有存在物中,人类是他最喜欢的,并希望其“生育繁衍,布满和征服大地;统治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行走的各种动物”。上帝赋予人类在宇宙中一种特殊地位,并明言由人类统治一切生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主张自然界的等级结构特征,即“植物为动物而存在,非理性的动物为人类而存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时代,虽然人类在世界上的位置的现代观念大大提升,但人类对动物的态度非但未有明显改变,反而在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论证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他看来,动物充其量就是一架无感觉、无理性的机器,像时钟那样转动,感觉不到痛苦。动物机器论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活体动物实验开始成为时尚,一度推动近代科学走向繁荣。一言以蔽之,这种带有强烈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人与动物关系不但根深蒂固,更伴随人类迈入工业文明时代,甚至延续至今。
不过,在人类中心主义这一主流话语之外,非人类中心主义也开始萌芽。十八世纪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质疑的最具代表人物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他是从人的角度论证动物伦理地位的第一人,认为判断人的行为是否合理应以该行为能否增进当事者的幸福为准,且受这种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的利益都应该考虑在内,并指出人类的道德关怀应诉诸在动物身上,减少对动物的痛苦并结束对动物的残忍行为。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欧美诞生了由亨利?塞尔特等人主导的一系列动物保护伦理学说和仁慈运动。不过其局限性在于关注的动物个体主要限于家畜和实验室中的动物,而且他们并未给出任何解决方案,反而在面对人类生活习惯时出现了退缩的迹象,如边沁总会降低论据的标准,用“仅因为我们喜欢吃肉”这样的理由为容忍人类食用动物开脱。但他们在超越传统的道德共同体方面迈出了艰难一步,为之后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说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二十世纪上半叶,人类在见证工业文明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被其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所困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种子开始孕育。德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t)在1923年出版的《伦理与文明》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敬畏生命伦理原则。他对伦理学重新加以界定,其核心是人类对世界及其遇到的所有生命的态度问题,即是敬畏人类自身和人类之外的生命意志,生命没有高低和贵贱之分。这一论断超越了传统的伦理学研究,将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囊括其中。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美国环保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中文版为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是其代表作,他提出的大地伦理学说是指由土壤、水、植物和动物等组成的生态共同体。他摒弃了先前那种人类对共同体的征服者角色,代之以普通成员与公民的角色,而且人类应当负有维护大地金字塔结构的积极义务,尊重每一位共同体的成员。敬畏生命和大地伦理学说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奠定了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基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球生态严重恶化,各种环境问题凸显进而引起学术界关注,非人类中心主义遂发展成为新的时代议题。哲学界和伦理学界试图打破传统学术研究的界限,将道德关怀的范围从人类社会扩展至非人类社会,这一过程首先是从动物开始的,动物的权利问题成为环境伦理学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突破口。在各种关于动物伦理的现代讨论中,澳大利亚著名道德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最早中文版本为孟祥森、钱永祥合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因其鲜明的逻辑性和实践性而最具影响力,同时最具争议性。
彼得·辛格分别在墨尔本大学和牛津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三十岁就开始其学术生涯,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纽约大学等。他曾是国际生命伦理学会的创始人,在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理论建构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辛格自任教以来著述颇丰,发表专著达二十余本,如《饥荒、富裕与道德》《实用伦理学》等,他对生命伦理学涉及到的生死问题、动物权益问题等都有所研究,并一直与环境组织合作,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贫穷、保护环境和改善动物生存环境。辛格关于动物解放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动物解放》一书中,该书初版于1975年,再版于1990年,迄今为止已经被译成二十余种语言出版,行销世界达百万册,并被誉为“动物解放运动的圣经”“生命伦理学的经典之作”。

《动物解放》共分六章,作者开篇就在借鉴边沁功利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支撑全文的伦理原则,即“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人类作为道德关怀的主体,必须平等地考虑所有生命个体的道德利益,而感知痛苦能力的界限是人类扩展道德关怀的正当合理的唯一边界。作者充分肯定动物感受痛苦的能力,依据上述伦理思想在接下来两章主要通过分析大量动物实验数据报告和工厂化饲养方式,对人类文化中固有的“物种歧视”(Speciesism)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揭露。作者列出的数据和例子令人触目惊心,如1986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每年用于研究实验和教学的动物数量在一千七百万至两千两百万之间;美国大公司控制的工厂化养鸡场每周宰杀肉鸡量达一亿零两百万只,而肉鸡密闭幽暗笼养法、断尾养猪法、限制贫血小肉牛活动的饲养方法等都毫无例外地剥夺了动物本应享有的五项基本自由:转身、梳毛、站立、卧倒和伸腿。接着作者在梳理古希腊至近代时期人类对动物的态度之后,提出要从人类思想根源深处放弃对动物的虐待,消除人类的“物种歧视”,并以“做素食者”作为解放动物的现实解决路径。最后作者回顾了动物解放运动在与各种反对学说进行的抗争中所取得的进展。
《动物解放》带来的思想革新和动物解放运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如辛格2003年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动物解放三十年》所言,“这项建立在公正和公平基本原则上的事业在过去三十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动物解放和动物权利组织不断涌现,社会大众对集约化养殖、动物实验等虐待动物行为的了解逐渐增加,英、美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开始采取强硬立场,露华浓、雅芳等公司也试图进行动物替代品实验。总之,与先前对动物保护的嗤之以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对待动物的议题常常成为新闻,各种关于动物的纪录片被制作出来,如法国制作的纪录片《以动物之名》,揭露人类对动物的暴虐和残酷,倡导人们应给予动物尊重和同情。
然而,辛格的动物解放论在学术界引起的争议之大丝毫不亚于它所取得的成就。从其诞生起就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批判,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哲学家汤姆·雷根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被罗德里克?纳什称赞为是唯一能够与彼得·辛格相媲美的动物权利论者。雷根虽然赞同辛格将人类道德关怀诉诸动物,但否认必须建立在动物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这个前提上,而是以动物本身具有的权利和天赋价值作为他理论的支撑点,认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动物的态度。他对辛格信奉的功利主义的批判有两点,一是对功利主义而言,具有价值的是个体利益的满足,而不是拥有这些利益的个体;二是功利主义者选择的最佳行动方案,对每一个相关的个人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但对每一个其他相关的个体来说未必如此。雷根在动物权利运动实践上更加激进,他提出应全面禁止商业型饲养业、娱乐性打猎和把动物应用于科学研究。
不过,对于辛格来说,最具争议的当属他的生命分级学说。他认为生命个体拥有内在价值和道德关怀与意识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将生命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人格(正常人、黑猩猩等有理性意识者)、有知觉的生命(动物、人类新生儿和智障)和无知觉的生命(植物、怀孕不满十八周的胎儿),三者拥有的内在价值和道德关怀随意识发达程度的高低依次呈递减趋势,个体生命价值从神圣到可被剥夺。辛格还为这种观点进一步辩护道:“新生婴儿在理性和自我意识上低于非人类动物,因而他们并不比后者更具生命价值,至于残婴更没有生存权。”显然,辛格在提升动物道德地位的过程中降低了婴儿、残疾人等人的道德地位,甚至否定了智障残疾婴儿的生存权。此语一出,西方学界舆论哗然,新罕布什尔州圣安塞尔姆学院哲学教授苏珊·克兰茨所写的《对彼得·辛格伦理理论的批判:人类尊严的重要性》一文,从人类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出发对辛格进行批判。辛格的“残疾婴儿安乐死理论”更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1989年至1991年间甚至引发了一场席卷德语系国家的抗议运动,即震惊世界的“辛格事件”(Singer-Affair)。
实质上,动物解放理论除招致非议外,其本身还存在着理论局限和现实解决困境两大难题。第一,功利原则和平等原则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前者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后者是对所有的生命个体进行平等考虑,显然,二者无法同时兼顾,人们在选择那种能带来最大利益总和行为的同时往往不得不以牺牲某些个体的利益为代价,这与平等原则相悖。第二,辛格将对痛苦的感受性作为衡量是否被纳入道德关怀的标准具有片面性,因为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看,痛苦与快乐并非大自然价值的唯一尺度。再者,他的出发点仅是动物,植物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则被排除在外。第三,素食主主义的解决方式违背了人类原本的生态属性。从历史来看,人类的肉食习惯是由于长期进化而形成的,且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素食主义必然要求全面改变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这具有很大的激进性。另外,世界大量工厂里的动物是经过人类长期驯化的,它们已然基本丧失了在野外自然生存的能力,重回自然必定无法生存,这将是另一种形式的痛苦。最后,若继续推导下去,植物是否也需要解放?素食的对象也有生命,这又将如何作答?从实质上来说,辛格的素食主义不过是继续归谬,将导致极端主义的生态法西斯主义,人类也将不复存在。
除动物解放论外,西方哲学界和伦理学界纷纷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致力于寻求二者之间关系的价值伦理原则和谋求合理的解决路径,先后出现了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和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两个思想流派,若说动物解放论在人类跨越道德界限的道路上走出了一小步,那么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则分别跨出了一大步。
生物中心主义的创始人是施韦泽,如前所述,他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认为生命没有等级之分。这一原则后来由美国学者保罗?泰勒发展成以尊重自然为特征的环境伦理学,主张一切非人类生命体的天赋价值和权利都应获得平等尊重。由此可见,生物中心主义突破了动物解放论的“感受痛苦力标准”理论的局限,将包括一切动植物在内的大自然中的所有生命物都视作价值主体,从而纳入人类道德关怀的范围,并用生命平等原则代替了辛格的生命等级观念,进而为合适的动物解放方式提供了可能性路径。但它仍具有局限性,因为生物中心主义将道德意义的标准设定为有生命的个体,但却否认这些由无数生命个体组成的联合体如生态系统具有道德意义。另外,依照“生命是有目的的有机体”这一原则,每种生命有机体都有一种内在的自我目的,有利于实现这种目的的行为都是善的,因而当面对猛虎捕捉人类为食物等现象时,生物中心主义则将其视为生命体的一种自保行为。显然,这种解决路径与人类利益相悖,并非可取之道。
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伦理学困境应如何解决?换句话说,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合适的“尺度”作为衡量标准。生态中心主义或许能对此做出回答。生态中心主义在将人类道德关怀从生物个体扩至生物物种的基础上,最终的落脚点在生态系统,这是对动物解放论和生物中心主义的一种超越。利奥波德是这一学派的首创者,前面谈到,他倡导人类是共同体中的一员,人类对这个共同体负有直接的整体主义式的道德原则和义务。他把大地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视为最高的善,同时提醒人类对共同体的干预不应过于激烈。而后,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吸收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从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创立了西方环境哲学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价值论环境伦理学。其代表作为《哲学走向荒野》,从自然系统承载着多种价值出发推导出应该给予整个自然界以道德和价值,进而论证人类应该负有遵循并保存自然价值的义务。这种将动物放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考虑的方式,或许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人类道德进步的历史,也是道德关怀对象不断扩大的历史,从动物解放论、生物中心主义直到生态中心主义,道德关怀的范围从动物、生物进而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从而给予整个大自然以道德和价值的意义。回顾辛格的动物解放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远未达到生态伦理学所预定的目标。不过,辛格的理论仍有其魅力所在,从诞生之时就是以批驳人类中心主义为己任的,而那句“动物的解放是人类解放事业的继续”尤其发人深省,让人们叩问自己内心:何谓真正的道德?最后,人类必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构建生态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将弘扬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才能有效应对当下的环境危机,进而规划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届时,真正意义上的动物解放才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