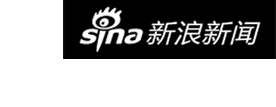生于1976·唐山
说不清的一代人
范震玲从不过生日。
她觉得尴尬:我出生,家里却死了三口人,是庆祝我还是纪念他们?
1976年7月28日,范震玲出生第19天,凌晨3点42分,唐山发生7.8级地震,23秒钟后,这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夷成废墟,24万余人遇难,包括范震玲的爷爷、奶奶及当年15岁的姑姑。
40年了,和当年所有新生儿一样,范震玲开启自己的“四张”岁月,成为家中的顶梁柱。
她不再向长辈追问劫后余生的故事,也不会刻意去给后辈讲述那些经历。大地震的记忆,随着时间而稀薄。
“老人都经历过,小孩儿又不懂。”他们,夹在中间,经历过却又说不清的一代人。

7月26日,唐山大地震纪念墙前。一名男子手捧鲜花,朝向墙上名字望去。摄/吴皓
名字带“震”,被经常讲述的出生故事
“对,1976年生的,地震的时候我19天……”
“是震中,受灾了,爷爷、奶奶、姑姑没了……”
名字里带“震”,初中时有同学笃定地问范震玲:“你地震那年出生的吧?”
走出唐山,每见到一个外地人,范震玲都要讲一遍地震的事,“很多人印象中好像唐山只有大地震。”
后来到外地上大学。别人第一个问题是家里是不是市区,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家死人了么?”
范震玲会一股脑全告诉他们,省得一直问。这,几乎成了她大学几年的困扰。
江洋的名字里不带“震”,但也绕不过这一宿命。“外地人都会问地震的事儿,我就讲我怎么被救出去的。”
江洋出生于1976年5月16日,地震前73天。
那时,江洋和父母、哥哥住在唐山老九中的家属院内,现新华贸附近。
“当时我们都睡一炕上。地震刚一晃,我妈就醒了。”母亲抱起江洋就往外跑,跑到门口时,地晃得厉害,江洋被母亲一把顺到院里的木头椅子底下,椅子帮他挡下了几块石头。
起身过程中江洋的母亲一巴掌拍醒了身边的丈夫。
“我爸刚坐起来就被地震的纵波从炕上颠到缝纫机下面,捡了一条命。”5岁的哥哥不幸成为家中最小的亡者。
天亮时,江洋与父母被邻居先后救出。除了5岁的哥哥,江洋的姥爷与大舅妈不幸遇难。
江洋没有叫“震”,但从小班里就有很多叫“震”的同学。“叫‘震生’‘抗震’的特别多。”
自降生之日起,地震便成为他们身上无法摘下的标签。

地震前出生的江洋,名字里不带“震”,但常被外地人问地震的事儿。摄/刘可
“全村除了我俩,当年震前生的全死了”
当年在唐山活下来的孩子,震前出生的被叹命大,震后出生的被说幸运。
刘苗生于地震前101天,属于命大的一波。唐萧震生于震后40天,被归为幸运的一波,称为“震漏儿”。
整个岳各庄村,除了刘苗和二叔的孩子,当年震前出生的,都没有活下来的。
唐萧震所在的将军坨,当年震后全庄只有他和另外一名女童出生。
范震玲上学时,觉得那届学生普遍偏少。“初中时,我们这届4个班,上届6个、下届7个,很多学校都是。”
江洋当时所在的机场路小学,同届有6个班,而到后两届便多到了14个班,初高中也是如此。
江洋觉得震后两年的孩子多,跟唐山本地家庭“补漏儿”和外来支援建设人员有关。
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家庭多半会在震后再生一个,这波孩子被称为“补漏儿”。江洋的妹妹便在这种情况下出生于1978年。
震后外来援建人员的子女也随行来到唐山上学。江洋记得自己同学中,四川、东北口音的都有。
在那一届中,同样常见的还有孤儿和伤残同学。江洋还记得班上有个同学姓“党”,是孤儿,老师会多关照些。
范震玲小学时,有个女孩左小臂缺失,“胳膊肘下面就剩一块肉,那时候觉得挺正常的,没个手、没个脚也不新鲜,都一起玩儿。”
他们都生在大地震的1976年。没人觉得有什么特殊,也没觉得地震有什么特殊。幼年的他们会用轻松的语气问起:“地震时你们家死人了没?”也会自然地回答:“死了,我姥姥姥爷”或者“我爷爷奶奶。”
对于他们,那只是一段没有记忆的过往而已。
就像江洋说的,自己从小知道哥哥地震死去的事情。家里偶尔说起,江洋听着,就像听大灰狼的故事一样平淡。

刘苗每到一个新环境,都会注意屋里的灯泡。灯泡一动,得赶紧躲。摄/刘可
再遇“地震”,老师抱着话筒往下跑
唐山大地震最近一次余震发生在2012年,36年之后,4.8级。
直到现在,每年入夏,只要天气特别燥热,唐山的出租车司机都会说:“是不是要地震啊?”唐萧震的母亲,在每个7•28前都觉得要“晃荡晃荡”。
刘苗读小学时,就记得唐山常有地震传言,每家每户都把值钱的东西放在身上。到晚上往街上一看,街坊邻居都睡在外面。
“全村只有我爸睡屋里”。刘苗的父亲曾是一名地理老师,常说一句话:“大的跑不了,小的倒不了,都是命”。
江洋的父母也是很害怕地震。每次有传言,他们就会跑到空旷的地方,和整个小区的人一起,坐那儿等着震。
“我才5、6岁,听到爸妈在说粮票什么的还在楼里,要不要拿出来。”江洋现在想起觉得很可笑。
小孩子们到处乱跑,家长们就嘱咐“离楼远点儿”。大人讨论要不要回去时,江洋也会想,会不会回去就震。
江洋小学时,一次开阳台门正好遇到地震。他撞到护栏上,胸口疼了好几天。
高中时,江洋记得刚下早操,突然地震了。他看到老师抱着话筒就从主席台上往下跑。而食堂里,盛豆浆的大师傅也是撇了豆浆就跑。没经历过大地震的学生,只是懵在那里。
有时走在路上也会震一下。江洋和同龄的孩子都麻木了,但有些大人依旧紧张。
范震玲觉得地震就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震起来也懒得往外跑。“唐山在地震带上,总那么震都习惯了,有时候看朋友圈才知道。”
刘苗不一样,每到一个新环境中,他会像冯小刚电影《唐山大地震》中的方达一样,注意屋里的灯泡,灯泡一动,往往就是地震,得赶紧躲。

一群在地震纪念墙前寻找亲人名字的市民。40年已过,当年的幼儿已经中年。摄/吴皓
被选择的幸存者,“我给了你第二次生命”
2010年上映的《唐山大地震》将1976年出生的唐山人割裂成两派。
一派为了追寻当年最直观的场景去看,把长辈讲述的大地震故事转换成立体的画面;一派则因不愿直面那段历史而坚决拒看。
范震玲是前者,江洋是后者。
“我完全不想看,很有抵触,我觉得心里会不舒服。”但他却看所有电影相关的新闻,也知道大概剧情。
曾有人在办公室看这个电影,江洋听到部分剧情。“尤其是在两个孩子间做选择时,我心里特别不舒服。”他会想起,地震时母亲毫不犹豫将他抱出去,5岁的哥哥却就此丧生,他成为幸存的那一个。
“当然我小,刚两个月,就睡在她旁边。但我哥就这么没了,心里特别难受。”电影的情节会让他难受。
江洋曾以为这件事对于他而言早已被平复,“可一旦电影摆在你面前,还是会产生反应。我这样经历地震还没有记忆的人,伤痛也一直鲜活。失去亲人的情感,不容易翻篇儿,不是时间就能轻易淡忘的。”
江洋的父母也没看过这个电影,吃饭时说起却比他还淡然。江洋通过照片知道哥哥,知道他特别灵,知道他看个电影回来学什么像什么。
父母很少再提起那段往事。但每当自己犯错时,母亲总会用“我给了你第二次生命”或者“当初要没把你救出来,你都没有了”来训他。
“我一直闹不清我在家是老大还是老二,如果有个哥哥,也许我的性格会更少爷羔子一点,父母可能也会更宠我一点。”
“其实挺享受有这么个哥哥的,就是没了。”

在家制作家具的唐萧震。当年震后全庄只有他和另外一名女孩出生。摄/吴皓
断层的记忆,“地震真有那么惨?”
时间过去40年,经历过大地震的人,正从衰老走向死亡。
江洋父母一代,会偶尔提起,当年被自己从房梁、瓦块下救出的某人还活着,现在好几十岁了。
而江洋这代,记忆都来自长辈口述。已被模糊的历史,他们很难再复述给下一代。况且,“也不是什么美好的记忆。”
以前过年,家里的叔叔凑在一起吃饭还会聊起地震的事儿,范震玲觉得新鲜,“我说全都倒了?他们就讲那墙全都压在我爸身上了怎么怎么的。”
“我曾经问过我爸,‘爷爷奶奶没了,你不难受?’我爸瞪了我一眼,没搭理我。”越到后来家里说得越少。
江洋还留着当年那把救过自己一命的木头椅子。2002年,江洋结婚,他把椅子从父母房子里搬到自己家中。
“椅子上面还有石头砸的坑,对我来说有一些特殊意义。至少冯小刚说拍电影要捐当年的东西,我不舍得。”
儿子曾问起,他会说,“这椅子当年救了你爸一命。”但除了被救,以及看过的一点史料,江洋能讲给儿子的也不多。
与江洋同样经历的耿震,被儿子问起时则会直接说:“汶川地震网上有录像,你上网看看就知道。唐山地震,比汶川惨多了。”
耿震的孩子十五岁,去年去抗震纪念馆参观。回来后,儿子问耿震:“真有那么惨?”
-

纪念墙上刻着遇难的市民名字。这座纪念墙建于2008年。摄/吴皓
-

抗震纪念墙前,一座有地震发生时间的时钟雕塑。摄/吴皓
-

40周年前夕,抗震纪念墙的跟前摆放着一束束前来拜祭的鲜花。摄/吴皓
-

一对夫妇向刻有亲人的纪念墙鞠躬。摄/吴皓
-

纪念墙上刻着在那场地震死去的人的名字。摄/吴皓
-

纪念墙前,一位老人用手指着墙上的名字告诉另一位老人。摄/吴皓
-

放在纪念墙前的鲜花。摄/吴皓
-

一名男子站在纪念墙前,若有所思。摄/吴皓